陈一娜网红是干什么的,网红提子和陈一娜是什么关系
DouJia 2023-01-14 14:30 317 浏览
摘要网红提子和陈一娜是什么关系:在元以前的律文中网红提子和陈一娜是什么关系,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作出相应的规定。自元代以后,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代的律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代,虽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告状,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讼方面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406件妇女参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女与抱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律例规定、官方认识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通过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是限制妇女参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女或他人竟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名捏禀”之事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造成如此结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乃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三种因素又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
关键词:《南部档案》;清代民事诉讼;妇女;抱告
在传统社会,男性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妇女则常常在历史长河中“缺席”。要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让她们“在场”,历史人类学也许是一条可以尝试来解决问题的路径。通过对州县档案所保存的大量涉及妇女诉讼的档案的研究,不仅是实现这一路径的有效方式,而且对我们理解传统法律和司法实践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以清代四川南部县司法诉讼中的妇女与抱告制度为视角,以期再现妇女在司法传统中的历史记忆。
现有的研究中,胡震《诉讼与性别》一文涉及了晚清京控中妇女与抱告的情况,其论证侧重于探讨妇女在各种利益需求下的诉讼行为,故不能苛求文章去深入研究妇女与抱告制度的相关问题。邵雅玲、吴欣、阿风利用档案、档案汇编、判牍或官箴书研究了台湾淡新地区、河北宝坻县、四川巴县等地妇女的诉讼情况,对本文的研究启发很大,但由于对律例,特别是对律例产生的时间梳理不够,时常把律例中没有规定的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由于利用的档案案例少,他们的研究没能展开和深入。更由于案例的样本少,无统计学的意义,得出的结论也多不足为信。最近姚志伟的博士论文《清代抱告制度考论》,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最为精细的论文,特别是对抱告制度历史渊源的考察最为精到,因其研究旨趣是对抱告主体的全方位考察,又因实际看到的档案数量不多,一些提法仍欠准确。因此,无论是从法制史还是从地域史的角度,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仍有必要。为此,笔者从《南部档案》中选取了406件档案作为研究的基础,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
一、妇女诉讼权利之限制
(一)限制妇女告状之源起
在早期的律文中,对部分人群告状有限制,但妇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席”,没有进入官方的视线。
《唐律》对告状者的限制主要是针对老、幼及身体有残疾的人:
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官司。受而为理者,各减所理罪三等。
《宋刑统》沿袭了这项规定。据阿风的考察,宋初几次发布命令,对于老人及笃疾之人的告状做出规定,但仍没有专对妇女的内容。北宋末年,有地方官规定“百姓年七十或笃疾及有孕妇人,并不得为状头。”此规定视“孕妇”为不堪受刑的人,禁止出面诉讼。直到南宋后期,任江西抚州知州和江西提刑的黄震(约1204~1276)在其《引放词榜状》中提到“非户绝孤孀而以妇人出名不受”。照此意,如果不是户绝、孤孀,妇女出名告状一律不受。但这似乎只是黄震个人的做法,在其他时人的著述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规定。
到了元代,对妇女告状始有法律的规制。元皇庆二年(1313),规定:
告争田土、房舍、财产、婚姻、债负积年未绝等事。……(妇女)若或全家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然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所告是实,依理归结。如虑不实,止罪妇人,不及代诉。……凡妇女代替男子经官辨词,会准所言,通行禁止。若果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另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不拘此例。如蒙准呈,偏行照会。相应都省准拟,依上施行。
此条给了我们以下资讯:(一)妇女在全家无丁男的情况下,可以让“宗族亲人”代诉;(二)如果妇女所告不实,则罪妇人,不罪及“宗族亲人”中的代告者;(三)妇女不能代替夫出讼。对于“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别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允许妇女自己起诉。由此可见妇女被纳入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群体之一,其诉讼行为有所限制。
到了明代,《大明令》对妇女的诉讼范围和诉讼权利有了进一步的明确:
凡年老及笃废、残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从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凡妇人除犯恶逆、奸盗、杀人、入禁,其余杂犯,责付有服宗亲收领听候。一应婚姻、田土、家财等事,不许出官告状,必须代告。若夫亡无子,方许出官理对。或身受损害,无人为代告,许令告诉。
后朱元璋颁行《大明律》,将妇人与老、幼、废、疾者同被列为限制诉讼行为者:
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逆叛、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官司受而为理者,笞五十。
《大清律例》沿用了此“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律下的“例”中,删除了“妇人”。且看:
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依照此例,妇女的诉讼权被完全剥夺,甚至遇到“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的情况时,也没有告状的权利了。事实果真如此?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其《读例存疑》中写道:“明例原系两条:一老疾;一妇人。是妇人亦准代告也。删除此条,若一切婚姻、田土、家财等事将令自告乎?抑一概不准乎?殊嫌未协。”薛允升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妇女告状被限制的事实是无疑的。
《大清律例》
(二)限制妇女告状的原因
之所以要限制妇女告状,现通行的观点是妇女无独立诉讼能力。但此结论是西法东渐后的产物,不足以反映传统社会的实态。本节拟在考察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原因。
在《元典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何以限制妇女涉讼的部分原因。
照得,元告,被论人等,于内有一等不畏公法素无惭耻妇人,自嗜斗争,妄生词讼,椿饰捏合,往往代替儿夫、子侄、叔伯、兄弟,赴官争理。及有一等,对证明白,自知无理,倚赖妇人,又行抗拒,起生侥幸,不肯供说实词,甚至别生事端。在后体知,复有一等年幼寡妇,意逞姿色,故延其事,日逐随衙,乐与人众杂言戏谑,勾引出入茶肆、酒家,宿食寄止僧房、道院,中间非理无所不为,习以为常,官不为禁。甚矣!妇道有伤,风化合无,今后不许妇人告事。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所告是实,依理归结,如虚不实,止罪妇人,不及代诉……本部议得,妇人之义,惟主中馈,代夫出讼,有违礼法。
《元典章》
由上不难看出,之所以被限制,在时人看来,是她们的行为所致。这种行为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一些妇人不畏公法,素无惭耻,妄生词讼。二是恃妇呈刁,无理取闹,甚至代替儿夫、子侄、叔伯、兄弟,赴官争理,别生事端。三是一些寡妇凭其姿色,故延其事,日逐随衙,杂言戏谑,大伤风化。平心而论,对这三种行为稍换言辞,如将“凭其姿色”换成“凭其能事”之类的,也可称之为男性的表现。为什么唯独要对女性加以限制呢?
首先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家长制社会。瞿同祖的研究明确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族的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子孙,未婚的女儿孙女都在他的权利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的手里。男尊女卑,以男为贵,女人在三从主义之下,自生至死皆处于从的地位,无独立意志可言。“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妇女的生活空间被限定在家庭里,家庭成为她们生命的全部舞台。她们到庙里烧香、戏园看戏都会被认为影响社会秩序而严加禁止。如光绪二十五年,保宁府在其谕令中称“保属风气,每有戏会,女多于男,年轻妇女,抛头露面,不知羞耻”,于是要求所属各属“劝谕民间,力讲妇道,以维礼教而挽浇风”。不独保宁府,在其它地方也同样禁止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如在四川巴县禁止妇女在清明时节出外踏青,在江苏省甚至将禁止入馆喝茶也写进了省例,“倘于妇女入座,即属故违谕禁,拉提店伙重惩,枷号通衢示警。”传统的妇女观不仅要求妇女本人要顾其颜面,而且也要求他人维护这一观念。如此一来,限制妇女告状则是顺理成章的结局。

其次是防止妇女利用法律给她们的特权“恃妇呈刁”。有律为证,顺治三年《大清律例》在前《明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的律中另加了小注:
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以其罪得收赎,恐故意诬告害人)。
“以其罪得收赎,恐故意诬告害人”即是小注内容。如前所述,在此律下的例中删去了“妇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妇女凭法律给予的优待故意诬告害人,致使官方对妇女参与诉讼的权利多了一分警觉。
清律对妇女的优待主要有以下几条:
妇人尊长与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为首,仍独坐男夫。
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本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
妇女有犯奸盗、人命等重情,及别案牵连,身系正犯,仍行提审;其余小事牵连,提子、侄、兄弟代审。
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留裤)受刑,余罪单衣决罚,皆免刺字。若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一家人共犯罪时,不坐妇人,而独坐男性,即使罪坐本妇,女性大部分罪名在定罪后均可收赎妇或赎罪。妇女在监禁方面也享有特权,除人命、奸盗等重大犯罪外,妇女可不受监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仅徒流可以收赎,甚至充军这样很严重的刑罚,妇女也可收赎。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法律给妇女诉讼有诸多优待,可为何诉讼权反而却愈加限制,甚至在律文中被删除?小注给了我们答案,是因为“故意诬告害人”。考察史实,制度的规定无疑助长这股“诬告害人”之风。在当时女性即使诬告反坐,所坐之罪有不须罚者,即使罚者也多可赎,风险极小。对于收赎而言,其罚银数量甚微。光绪年间刑部就上奏,妇女罚赎银数太少,不足以惩戒。
是妇人本人故意诬告他人,还是妇女被他人利用她们的诉讼优势去诬告他人?《大清律例》虽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法律背后的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这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我们可以推断,妇女或他人正是利用了妇女的这种优势频繁地涉及诉讼,而且故意诬告他人。此种情况在官方奏折、档案等资料中多有指出。如在清代名臣李星沅在奏折中言:“有一等无耻妇女,稔知犯罪律得收赎,无端混告。”正是因为妇女凭借法律上享有的优待,造成混告、诬告之风日益猖獗。可以想见,妇女的诬告之风远远超过“年老及笃疾之人”,以至于落得在“例”中被删除的结局。这样一来,其诉讼权的一再被限制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
(一) 妇女诉讼需有抱告
妇女的诉讼权虽被限制,但尚没有被完全禁止。最近的一份研究否定了先前学人认为“抱告制度始于周”的论断,认为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但没有实质上的传承关系。抱告制度在宋代已经萌芽,特别是“乾德诏书,七十以上不得论诉,当令宗族中一人同状,官乃理,若实孤老即不在此限”和“民年七十已上及废疾者,不得投牒,并令以次家长代之”的规定与后世抱告制度的运行很接近。到了元代,这一制度基本定型,明清时期逐渐完善。
但第一节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抱告制度渊源的通论对妇女而言,并不具有普适性。妇女告状需有抱告的规定始于元代,明代也通行此政策,但到了清代,此规定不仅没有完善,反而在法律文本中消失。那么清代妇女可告状吗?她们告状需有抱告吗?
道光六年,宗人府具奏,对宗室觉罗妇女,饬禁宗室觉罗妇女呈控,并酌定惩处专条一折,并被纂辑为例:
凡宗室觉罗妇女,出名具控案件,除系呈送忤逆照例讯办外,其余概不准理。如有擅受,照例参处。倘实有冤抑,许令成丁弟兄子侄或母家至戚抱告。无亲丁者,令其家人抱告,官为审理。如审系虚诬,罪坐抱告之人。若妇女自行出名刁控,或令人抱告后复自行赴案逞刁,拟结后渎控者,无论所控曲直,均照违制律治罪。有夫男者,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身,折罚钱粮。
由上可知宗室觉罗妇女在实有冤抑的情况下,可以“令成丁弟兄子侄或母家至戚抱吿”,若无亲丁,则令其家人抱吿——这说明宗室觉罗妇女有用抱告告状之事实。而当年在《大清律例》中删除“妇女”的时间无按语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例”出台之后,即顺治三年后。律学著作《大清律辑注》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刻,作者即清代律学大家沈之奇当年在“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下注道:“律不得告而例许代吿者,恐实有冤抑之事,限于不得吿之律,致不得申辩。故立此代吿之例,则有冤者可以办理,诬吿亦得反坐,所以补律之未备也。”这种遇有冤抑可用代告的说法与言宗室觉罗妇女的情况相差无几。这能不能推测随着时间的后移,时人普遍认同一般妇女同宗室觉罗妇女一样可以由他人代告呢?尚难确定。
《大清律辑注》
但另外的途径却暗含清代妇女在有抱告的情况下可以参与诉讼之意。同治十二年编纂的《大清律例会通新纂》之“越诉条”规定,“生监、妇女、老幼、残疾无抱告者不准”。这项规定,也多见于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状式的《状式条例》中。现列举几例:
由所列《状式条例》可知,抱告主体范围在不同的地方、在同一地方的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在不同的规定中,不管如何变化,妇女始终位列其中。
通过对南部县的《状式条例》的动态考察,我们发现了出人意外的现象,在乾隆某些时期的状式条例中,规定“绅衿、妇女无抱告者不准”,而“绅衿”和“妇女”正好弥补了当年《大清律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例中“年老及笃疾之人”以外没有规定的部分。换句话说,抱告主体在嘉庆后为“绅衿、老、幼、残废、妇女”的规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概念的周延,并无实质性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有清一代,除了谋反、判逆、子孙不孝等涉及干名犯义的重罪,及抢劫、杀伤之类的刑案准许妇人亲告外,其它户婚田土地一类的民事纠纷,妇女一般不得亲告。如果要进行诉讼,则需要抱告。这种推测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制定的《大清现行新律例》中得到了验证,此律“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条中规定:
年老及废疾之人,并妇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若妇人夫亡无子,或身受损害无人代告者,听许入官告诉。
此处为何要加上“妇人”二字,沈家本等人解释道:
臣等谨按:此仍明例,原系两条,一老疾,一妇人,嗣将妇人一条删去,第向来办法,妇人仍责令遣抱,自应增入。
虽然删去了,但妇人仍责令遣抱却是“向来办法”。所以在法律上虽消失了,但实际操作却无变化。
(二)对司法档案中妇女与抱告的考量
对诉讼中妇女与抱告的考量是基于我们从《南部档案》中统计出的354卷406件档案。406件档案基本涵盖了现存档案中的所有婚姻档案。同一卷档案原则上只择取一件档案,但在统计时考虑到妇女、抱告、出庭、差唤等几个因素,因此也保留了少量的相同案件,主要是考虑虽为同一妇女但在不同的案件里有不同的抱告、同一妇女多次参与诉讼虽抱告相同但告状方式不同、同一案卷中多名妇女参与诉讼、档案缺损但列有妇女参与堂审的情况。
1.年龄
(1)妇女年龄
对《南部档案》参与诉讼的妇女的年龄统计中,406件档案除去年龄不可考76件,除去两件以上档案为同一人的12件,及有5件档案每件均有2名妇女同时参与诉讼,获取有效档案资料322件。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为78岁,平均年龄为49.35岁。妇女参与诉讼的年龄段集中在30—64岁。与《黄岩档案》相比,平均年龄大致接近,相差不到2岁,但因《黄岩档案》案例少,年龄段的分布不及《南部档案》完整。
从档案看,所有参与诉讼的妇女没有一例为未婚少女,全为已婚妇女,而且90%以上为孀妇。
(2)抱告年龄
406件档案中,共获取抱告年龄资料420例,其中有94件档案为年龄不可考或同一人数次为同一妇女作抱的情况,实际获取有效年龄资料326份。326份中,妇女一人诉讼以两人作抱的有14件档案,妇女两人诉讼以两人作抱的有3件档案,没有发现两人诉讼以一人作抱的情况。
由于“绅衿、老、幼、残废、妇女”是诉讼的受限人群,所以他们不能作为抱告。对于老、幼年龄的界定,沈之奇在《大清律例》“脱漏户口”律后注为“十六岁以上成丁……十五以下曰幼,六十以上曰老”。据此,“老”以60岁为界。上表中《南部档案》、《黄岩档案》抱告最大年龄分别为58、54岁,均没有超过60岁的界线。故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这一规定是得到了遵守。
黄岩档案
但“幼”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沈之奇没有对15—16岁这个年龄段属于“幼”还是“成丁”做出界定,我们姑且把抱告的年龄放宽到15岁。从档案提供的实际情况看,仍有低于15岁的男性在作抱,南部县13—14岁作抱的有4人,黄岩县有14岁男性1人作抱。而从《南部档案》的情况来看,我们能大致推测被实际确定的允许作抱的年龄为16岁,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有多达18人作抱,也在于有可能把没到16岁的男性,在写状时写成了16岁,如第14目第452卷,孀妇王张氏以子王九林作抱状告娘家胞兄不顾兄妹之情,将其倒卖给他人作妻,状纸上将王九林的年龄写为16岁。但在其后的禀状中,却把年龄写为13岁。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南部县还是黄岩县,从批词上看,均没有对没到法定年龄的男性作抱的情况提出疑义。如“候唤讯究,粘附”、“着遵前批,赴场呈请核办,不得恃妇混渎,特饬”。《淡新档案》也有因抱告不符合年龄规定而不受理的案件,甚至在民事编第12606档案中,林杨氏竟以5岁儿子为抱。第32602件档案,黄钟氏以14岁儿子为抱,但淡水同知并未批斥,且饬传抱告。但在此档案中有因年龄未到不予受理的情况。如22608档案,抱告为14岁,衙门批道:“尔男年未成丁,应另遣抱告投到候讯领结,掷还。”只是此类案例为数甚少。
淡新档案
因抱告多为妇女的晚辈(有11例以孙为抱),所以抱告的年龄普遍小于妇女的年龄。从平均年龄看,《南部档案》提供的资料显示,抱告比妇女小17.2岁。
2.抱呈与妇女的关系
在上列统计表中,婿计入夫家(族)人。《南部档案》案件不详主要是指档案缺省或不便分入夫家、母家的。缺省的档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只有供状。如7-419-993,从档案里只能分析出妇女是告状者,但因无告状,供状里也没有交待是否有抱告;二是本有状式,但状纸残缺,只能看到是妇告在诉讼,但看不到抱告是谁,在其它地方也无交待。如8-1030-1463。《黄岩档案》中,案件不详数主要是指没有写明抱告与妇女是何关系。《淡新档案》则是依阿风的既有研究统计而成,4件归入案件不详数是由于不明确抱告身份。
从统计表看,以夫家人为抱告占主导地位,南部县所占比例高达65.52%。这是符合宗族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在宗族社会里,“既嫁从夫”的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自嫁到夫家后,从心理上已把夫家作为自己的家,把夫家的亲属作为自己的亲属,她们的活动自然是以夫家为中心,在经济利益上也基本不与母家有牵连。
但在南部县,仍有21.67%是以母家人为抱告的。这种情况大致由以下几种因素所致:
(1)告夫家人。如第12目第541卷,孀妇周冉氏夫在时,曾乏嗣,先抱冉氏娘家胞兄冉裕宽女冉带香押相助身。夫故后,夫胞弟周正镐生奸,欺氏寡朴,谋氏财产,凭族将其子周秋元过继周冉氏承祧。至光绪二十一年,周带香年已及笄,但周正镐不准择户许字,勒氏还女。未达到目的后,便套佃氏业,恶霸佃租,绝氏衣食。更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串周正体纠率恶工杨定林同妻何氏等数人,偷开氏仓,抄拿谷粮、衣饰,逼氏改嫁。冉氏不从,周正镐遂将其逐出屋外,害其无靠。周冉氏多次投族甲周洪先、周正德理论,但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周冉氏便以48岁的娘家胞兄冉裕宽作抱状告夫家周正镐、周正体等四人。这是妇女为己事告夫家的情形,也有娘家为女儿在夫家受欺告女儿夫家之案。如第13目902卷,孀妇宋王氏就以“嫌逐押搕,叩唤究刁”状告女儿夫家张芝华、张芝荣、张文锐等三人。因为女儿许与张芝华之子张文锐为妻后,父子嫌其女笨拙,苦不当人,刻薄衣物,动辄毒殴,惨不堪言。光绪二十三年,文锐执刀行凶,其女归宁泣诉,后投鸣保甲邓正贵、范大寿理息,出约。但他父子俩嫌离心切,无故将女逐外,无踪,生亡莫卜。但他们恐要人,便先法制人,诬宋王氏倒卖,率族张芝荣等押搕钱五十串。宋王氏不甘,便将他们一并状告衙门。
(2)夫家人畏恶,只有求娘家人作抱。同治九年,东路积下乡马周氏、马陈氏告状就属此情况。状称两氏夫均故,同胞分居,均无后嗣,仅抱一子马万礼,且年幼。两妇立志孀守,但族恶马元保、马元喜欺孤押寡,希图绝业,逼令改嫁,两妇不从。于是将她们田地当与陈闰保、张自守耕种,并瞒吞当价钱,砍树。两妇无奈,控告县衙,获准差唤。但“伊等情虚,拖延不审,更支陈闰保等于九月二十四日将氏等未当已种地土复行耕翻,有赵喜可证。家族人等畏恶,莫何,只得各投娘家叔弟抱呈”,于是两妇各以娘家胞弟周宗位、胞叔陈文彦参与诉讼。
还有就是所告与夫家利益无关。
从以母家人为抱告的情况来看,若夫妻的组成形式是常态的一夫一妻制,妇女基本上为孀妇。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吴欣对妇女再嫁案件的成因分析所指出的,“当一个妇女失去丈夫,她也就失去了立足于夫家的根基,面对家庭、社会复杂的关系,她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母家”。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分析为何用母家人为抱。
考察清代在清末修律以前的律典,对妇女告状以何人为抱,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各个州县的状式条例也只对妇女告状须有抱告做了规定,也没有说明哪些人可以作抱。从《南部档案》保存的情况来看,以夫家人为抱的主要包括:子、夫侄、夫兄、孙、女婿、夫叔等,以母家人为抱的主要包括娘家堂兄、娘家堂弟、娘家胞侄、堂叔、亲弟兄、母舅等,甚至以自己的父亲为抱。除此之外,在南部县有3例抱告值得说明。有2例是以雇工为抱进行诉讼。1例是在第7目第427卷,敬梁氏、王蒲氏以同祖堂弟敬洪福、雇工敬朝金为婚事一同恳请息案,衙门批道:“两造既已凭证理息,准将原词注销省累,该差知照。”没有对抱告人的身份有任何异议。在第10目第933卷中,冯李氏以工姚永年诉马德泗。诉状称其嫁侯聚川为妾,侯聚川任陕西凤县知县时病逝,但衣木俱无,求同乡助银买地安葬。后欲归四川,但无资,于是改嫁冯在章为妾,归家数载“无亲人来往”。但马德泗乘夫往号清账,将氏诬控,要求邀何子正作证。衙门批词为“准邀质”。3例中,有1例是以近邻为抱进行诉讼。伊高氏夫故,仅育一女。胡国治串套刘国治娶为室。但刘国治已有妻室,伊高氏不允从。但胡国治恃其父为盐房典吏,欺其女流异孤无亲,估霸作妾。婚后遭殴打,苦不当人。于是以近邻黄国林为抱诉胡国治。从档案来看,之所以用近邻,是因为伊高氏无亲无戚,有一女但不能作抱。由前所述,一般而言,妇女告状可以夫家、母家人为抱告,若夫、母家皆无人,允许雇工、近邻等为抱进行诉讼。
但也有妇女不用抱告而进行诉讼的,只是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在所选的406件《南部档案》中,仅有3例。在第11目第472卷中,孀妇江汪氏“无子”,在告状中没有交待其他亲属状况。在第18目第1327卷中,孀妇赵曹氏称其翁、夫“相继而殁”,也没有交待其他亲属状况,其禀状被批准。在第16目第853卷中,66岁孀妇李杨氏仅交待了其子因充当保正时,对管下事务管理不善被责惩,笼囚示众。此妇要求开释儿子“归农养蓄”。李杨氏在恳状中也未说明是否还有其它亲属。我们尚不能根据为数甚少的3例判断何种情况可以不用抱告。不过,从其它地方的档案来看,则主要是孀妇无子时不用抱的情况。在河北宝坻县,孀妇王杨氏称“无子无人抱呈”。这一点在一些官箴书也可见,如“妇人必真正孀妇无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缓待者,方许出名告状,仍令亲族弟侄一人抱告”。
3.以子为抱告的情形
在406件档案中,不可考或以非夫、非母家人(徒、远邻)为抱告的有69件,有10件档案抱告数为2人(其中有4件夫家、母家各1人),因此可查的资料有347宗。其中以抱告为妇女夫家的资料为259例,为妇女母家的数据为88例。在以夫家人为抱告的数据中,以儿子为抱告136例,所占比例最大,占整个夫家比例的53%。
清律规定:“军民人等干已词讼,若无故不行亲赍,并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赍奏诉者,倶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壮丁问罪。”“妇人有子,年已成丁,即令其子自行出名,如仍以妇人出名,以其作抱告者,不准。”薛允升在《读例存疑》,就“妇女犯罪”条有按语道:“妇人犯罪,法原不轻于男子,而不许径行提审者,所在励廉耻、厚风俗也。乃家有子侄兄弟,而妇人出头告状者,亦应将子侄等重惩。”在一些地方的状式中也对此有明确规定,如在四川南部县,至少在道光至光绪年间,就规定“户婚田土等事,有兄弟、子侄,而妇女出头告状者不准”。“户婚田土等事,既有家长、兄弟、子侄,而妇女又复出头告状者,并将抱告惩责。”依照上述规定,凡家有成年儿子,即使夫亡或其他意外的情况下,也不得亲自参与诉讼,而是由成年儿子自己出面。这一点在一些判牍中也得到印证,如樊增祥就曾对一起由妇女起诉的案件批道:“尔既有十八岁儿子,何得隐藏不漏,恃妇出头?”不仅如此,在台湾淡新地区也有类似的处理。如在民事编21207案中,吴林氏以26岁之子男为抱,知县批道:“该氏既有二十六岁之子吴来成……不令出名呈控,反作抱告,而以该氏妇女涉讼,亦殊不合,特斥。”
《读例存疑》
而从上面的统计来看,实际的操作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张志京的说法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她认为,纵观古代女性的一生,“从父”毋庸置疑,“从夫”原则上也是不可动摇的,唯有“从子”难以成立。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法律规定看,除特例外,“从母”压倒了“从子”。“夫死从子”原本意义上是指夫死后,以儿子为参照系来确定妇女的服制。这是“从子”不应片面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服从、从属,而应看作是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对以儿子为代表、为承继者的夫家血脉宗族的尊重。中国古代女卑但又尊母的悖论现象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夫死从子”只限于对外关系。在家庭内部,儿子还必须服从于母亲的教悔。子须从母与“夫死从子”两者之间的关系,实是亲权与男权之间的一种制约关系,亲权附属于男权,但相对于儿子与母亲这种特殊关系而言,亲权又高于男权,两者之间实质上并不矛盾。

4.夫在的情形
传统社会,既嫁从夫,有夫在,诉讼自然是夫而不是妇的事。现有的研究指出,妇女在夫出外、有疾病、被关押或无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可亲自出面告状。而夫在无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州县官除对已出嫁女为母家的“冤情”出面呈讼的案件立案外,其余一般不予立案。在南部县,也多是类似的情况。
夫在外的情况,如张熊氏夫张大礼于“咸丰八年外贸未归”,以夫弟张大勋起诉。吕沈氏“夫吕东阳,出外贸易二十余载,杳无音信”,以女婿饶丕成作抱告状。周吕氏“夫远贸多年,概无音信”,便以子周兴元为抱进行诉讼。
夫在押的情况,如徐赵氏以娘家弟赵大柏起诉,其夫余炳连在押。兰张氏夫兰洪遂被王洪谟具控,被责惩收押在监。但夫在监染寒病沉重,兼有八旬迈母在家,衣食难保,于是以堂弟兰兴应作抱恳请开释。更有以在押的丈夫为抱的。如临江乡四甲郭孙氏因夫大、二胞兄郭朝文、郭朝开欺其夫在监守法,心存谋霸,将收到的当价钱不按原定的三股均分,还将郭孙氏的佃钱租谷霸收。其子仅两岁,母子俩日食难度,进退无路,便以夫郭朝宗为抱状告夫之兄弟。
夫有疾病或残疾的情况,如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马余氏“夫年老卧床,日久不愈,刻下命在呼吸”,故以子马志正作抱。袁梁氏夫“天生废疾,两手短缩,独脚跳行”,以夫弟袁文魁作抱。
除此之外,从《南部档案》来看,还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夫在,但妻受妾欺,妻以他人为抱,状告妾。如徐严氏不服翁姑管教,搬她娘家人打伤翁姑,被控。后判夫领回好和。但夫妾刘氏刁唆翁姑不给饭吃。“凡氏进食,即行百般辱骂。惨氏抚育四岁幼子,挨饥受饿,形容菜色。”后刘氏唆使氏夫骗氏私逃,具禀在案。万般无奈之下,以胞弟严先朋起诉。光绪十七年发生在金兴乡的一案也是同类案例。妇张姚氏发配张孝先为妻,已有二十余年,并生子女四人。后夫霸娶王氏作妾,便王氏淫悍残毒,“过门未久,恃宠生嫌,辄以氏朴子幼可欺,屡支氏夫将氏母子蹧践刻薄,无故殴辱。氏均含忍。王氏得意,尤欲逐氏母子出户”。便以娘家堂侄姚联培作抱状告王氏。
二是夫在,但受夫欺。如第10目第205卷,民妇范刘氏供:“小妇人发配范友顺次子范大勋为妻,过门岁余。这丈夫范大勋屡嫌小妇人本朴倭小,叠次刻薄衣食,小妇人均各哑忍。小妇人干兄李培之刁唆丈夫范大勋说娶赵氏与夫为妾,反将小妇人卧室另移别处,不许落屋。小妇人无奈,逃回娘家向小妇人父母叙说,父亲刘中周不服,叠投范有禄们耽承约理,翁父范有顺抗不从场,小妇人随同父亲投具红呈才来案把他们告了的。”
以上两类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夫妻感情不和睦。
第三类是在前夫死亡,妻再嫁,再嫁之妇不以后夫出面而多亲自告状。如第10目第203卷,后夫在,妇宋李氏告后夫子媳。案称宋李氏前夫文生左武成籍隶云南病故,生子左双贵。氏苦操守。治民宋朝发假冒营官,贪财谋娶,愿带氏子,誓言伊无子妻,肯允。套氏银衣烟土,外屈氏借王兴齐银二百两,图撇逼氏回籍,将氏银土置产,昧良瞎眼,纵子宋文朗同妻向氏管家,蹭嫌刻氏母子衣食,文朗生奸,今正以首饰支氏子外换作本贸易,冤被贼夺,即诬卷逃,毒殴氏子重伤,恨氏拢救,逆殴氏,齿落一颗。李秀春施救,文朗止给氏银十两,遂氏母子出外阻归,氏当赴控,遇李发孝劝拦,坦延至今。叠投保正董芝容理遣,横抗,惨氏母子异孤,衣食无靠,情惨挖心,匍匐乞首。于是以前夫儿子左双贵为抱状告宋向氏。甚至因后夫的刻薄,直接状告后夫。
还有一类就是夫死,后有男性赘户。因赘户败家而直接控告赘户。如若有官司,则不以赘户出面,而由妇女以他人作抱进行诉讼。如第18目第1321卷就是如此。
5.妇女与抱告呈状、被传唤及参加堂审的情形
按规定,妇女若要告状,一般情况下必须有抱告方能参与诉讼。清代官员也认为在司法过程中不轻传妇女。如万维翰就曾指出“妇女颜面最宜顾惜,万不得已,方令到官。”对此,汪辉祖也有类似的表达,“事涉妇女,尤宜详审,非万不得已,断断不宜轻传对簿。”袁守定认为凡词讼牵连妇女者,于吏票呈稿内除其名,勿勾到案。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养其廉耻,亦维持风教之一端也”。照此逻辑,状写完到衙门交状、堂审都是抱告的事,衙门差唤也只需传抱告就行了。已有的研究也认为“除非案情关系重大,妇女一般也不能出庭作证”。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从南部县的情况分析,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就交呈而言,有相当一部分仅由妇女交呈,而抱告没有“亲来”。据不完全统计,在406件档案中,仅由妇女交呈的有8件。由妇女、抱告同时到衙门递呈的有6件,仅由抱告递呈的有17件。对这部分统计是来源于状式上衙门盖的小戳(见下图),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案件并没有交待是由谁递呈的。
仅妇女交呈的戳记 仅抱告交呈的戳记
妇女、抱告同交呈的戳记
其次,从差票来看,以原告或被告涉案的妇女多被传唤,且抱告几乎一并传唤,此案例甚多,不再举例说明。除此之外,不为两造的妇女少有被传唤到案的。即便被差传唤,也不一定要到县衙参加堂审,如东路金兴乡四甲乡民徐张氏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作为“应讯”差传,但在其后的“点名单”上注明“不到”。这些事实与州县状式条例所要求的并不矛盾。如在浙江黄岩县,“非关命盗奸拐正犯,牵连妇女,不准”。河北宝坻县,“告奸性及命盗重案牵连妇女者不准”。四川巴县,“告案已准,续投呈词,又波及原案无名之人及牵连妇女另具投词者,一概不准”。四川南部县,“被告不许过三名,干证不得过二名,并非命盗奸拐,牵涉妇女者不准”。“被告不许过三名,干证不得过二名,并非命盗奸拐,牵涉妇女者不准”。“告奸情非奸所获奸,虽有实据,牵连妇女者不准”。到咸丰同光时期,规定“告奸情非奸所获,奸未有实据,任意牵连妇女者不准”。这些不同地方的状式要求都是同一层含义,即不得轻传妇女,不得任意牵连妇女。正如徐州知府阮祖棠所言:“妇女之不可轻传到案,前人言之屡矣。”“不轻传妇女”的确切含义是不轻传与案无关的妇女,“虚实候讯,毋庸率添妇女”即为此意。但不轻传妇女不等于不传唤妇女,她们并不是要被完全禁止在诉讼之外,虽然要顾其颜面,但与案情直接相关的,则需要被差传参加堂审,甚至连少女也不例外。清代方大湜在其《平平言》的一段话里即暗含了未嫁少女有出庭的事实。“闺女被官责打,已许字者,辱及夫家。未许字者,谁为聘问。颜面所系,即性命所关,如之何弗慎。余遇牵涉闺女之案,有万不能不责惩者,以手板授其父兄,饬令当堂责打手心,不特不令差役掌嘴,并不令差役捉手也。”
至于参加堂审的情况,《大清律例》于顺治十六年定例,并在乾隆元年改定:“妇女有犯奸盗人命等重情,及别案牵连,身系正犯,仍行提审。其余小事牵连,提子侄兄弟代审。如遇亏空、累赔、追赃、搜查家产杂犯等案,将妇女提审,永行禁止。违者,以违制治罪。”此例规定与《处分则例》相同。按此例之意,对于一般民事细故,不需要提审妇女,只需提子侄兄弟代审即可。在四川南部县,县官也有依此例照办的案例,如“准该抱告自邀鲜洪斌等来案质讯,该氏毋庸赴质”。“着该抱告等邀证来案备质,该氏勿庸到案”等等。但统观《南部档案》所存案件,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根据406件档案不完全统计,仅有妇女出庭的就有45件,仅有抱告出庭的13件,妇女、抱告均出庭的达91件。这充分说明了涉及两造的妇女多参与堂审的事实,尽管在部分档案中知县的判决也一再说明对妇女要顾其脸面、维持廉耻。
三、制度的反利用:从“恃妇逞刁”到“窃名捏禀”
清廷本限制妇女参与诉讼,又恐其有冤抑无处诉,而后有抱告制度之推行,可谓用心良苦。但妇女或他人却借妇女诉讼之优势,反其利用,扰乱司法,破坏秩序,却是当局者始料未及。
“恃妇逞刁”
“恃妇逞刁”,是指妇女本人无视法律之严肃性,恃其在诉讼中的优势肆意告状。吴欣的研究告诉我们,妇女在诉讼中拥有一些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她们坚持诉讼或她们诉讼时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最突出的表现是她们的“妇女”身份所带来的人们对其“无知”与“可怜”的认同。她们也常常利用这种资源在状式中述说自己的孤苦,以便在司法过程中赢得审判官的宽容与同情。这是当时妇女“恃妇逞刁”的一个诱因,但从《南部档案》的记载来看,妇女所“恃”的不仅仅是她们的“无知”与“可怜”,更是恃清律对妇女的优待,特别是收赎。正是由于妇女有收赎之权,她们才无所顾忌,恃“妇”逞刁。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东路金兴乡四甲乡民徐应成以“乱霸纠索,叩唤严究”状告族叔徐国藩,称在他出外读书期间,叔“霸诱民妻至家,私通恋奸”,后又“喊伊家内歇宿不返,宛如夫妇”。根据被告及整个案情,有可能是徐应成欠徐国藩钱,以诬图赖。此状告到县衙,刑房收呈,并批准。十二月初一日,七十岁孀妇徐彭氏,即徐应成的婆婆,以徐应成为抱,同为此事,再次状告徐国藩。徐彭氏称“有族叔徐国藩仗恃武生,连香帽顶,勾诱张氏乱伦私通,今前被氏拿获。国藩推氏跌地,跑逃。氏投胞弟徐联芳等苦劝不改,氏亦忍恨莫何,兼之张氏娘家请族任夫处毙无异。讵料国藩色胆弥天,仍霸张氏刁藏伊家,恋奸不归,冬月初七夜,引同张氏纠众估拿嫁奁。氏投保甲看明,信知应成回归,投族理遣,横抗”。从状词内容看,说的是同一件事。从告呈者来看,先有孙徐应成告状且被受理,在此情况下徐彭氏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再恃妇、恃老禀状对方。
不仅是妇女本身,更在于其他人也看到了妇女在司法诉讼中暗藏的优势,为避免自己受罪,便钻法律的漏洞,“托”妇之名“告”己之事。
“支妇兴讼”
“支妇兴讼”,是指他人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支使妇女或托妇女之名兴讼。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东路崇教乡贾姜氏之夫贾耀栋作媒生奸,被敬显宗所告后,支妻以胞弟姜心坪作抱反告敬显宗。称显宗忽生歪议,将其夫“苦打吊拷,逼写退婚文约,并押礼人等各各受伤。民闻知骇异。望夫不归,四处寻觅无迹。温洪才因人财两空,与伊构讼。子杨反诬氏藏匿,逼民要人。具控氏夫,似此作童子婚姻,且属世谊。子杨不念师恩,图人聘金,嫌人门第,骗婚诬媒,实合邑未有。氏家儿小女幼,家事难理,不知夫生死存亡。为此泣叩,伸雪夫冤,沾恩无暨”。又光绪十七年九月,东路积下乡冯元富支冯向氏状告继母冯陈氏。而冯向氏夫亡后,因贫改嫁邓世宽为妻,与冯家恩义已绝。并且冯陈氏卖业,也与冯元富无干。在这种情况下,冯元富不应支其改嫁之祖母出名妄控。以至最后衙门堂断,冯元富“干犯名义”,受“笞责”,冯向氏不应受他人支使“挺身讧讼,着记责” 。
“窃名捏禀”
“窃名捏禀”,是指未通妇女本人知晓,被他人窃名告状。光绪三十三年,南路宣化乡民杜奉先便窃婶杜全氏之名控杜天馨、罗光荣等人。待差役差唤时,杜全氏称她改嫁严姓数载,“侄杜奉先令四月由省归家,邀伊商议告状,未允。后窃伊名呈控。回家复邀伊投审,亦未遂”。差役具禀县衙,言“杜全氏称未告状,抗案不到,现在患病,生死莫测,未敢强唤”。光绪九年,乡民杜何氏与陈夏氏互控案中,杜何氏称“情今十月三十日控陈万沛、万消泽一案,批证查理,万沛窃母陈夏氏名跟告……万沛不依理落,经原证何正顺等禀复,准唤,尚未出票。可恶万沛仍窃陈夏氏名跟禀”。
就妇女和他人滥用其优势,对制度进行反利用而言,在制定法律和司法实践占均有所规避,如限制妇女涉讼,罪坐代告。从衙门对这些案件的批词或堂谕来看,地方官员对此是知道且有所警觉的,他们在批词中多有“如虚处抱”、“姑候唤讯,实究虚坐”、“如虚,坐抱不贷”的批语。但实际对他们的依法处理却少见。如上述杜奉先窃名捏禀一案件,批词为“据禀杜奉先窃名捏禀,殊属胆玩!既经情虚逃匿,从宽,姑名深究。着即销案,以省讼累”。前部分语气强硬,但实际的处理结果却以销案结束,绝大部分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
结论
以往的研究常常给我们展现的是妇女不愿或很少参与诉讼,但通过对《南部档案》的研究表明,妇女在这一领域是积极的参与者,她们因不同的目的受这样或那样的驱使,频频告状。
在元以前的律文中,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做出相应的规定。自元代以来,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代的律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代,虽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告状,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讼方面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406件妇女参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女与抱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在律例规定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
纵观抱告制度从制定到执行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到了晚清,西风东渐,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限制也在逐渐发生松动,抱告的实际功能在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妇女不须抱告而直接参与诉讼成为迟早的事情。
通过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也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是限制妇女参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女或他人竟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名捏禀”之事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而造成如此结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当是重要的原因。
注明:原文发表在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8期,2010年,第106-131页。由于篇幅限制,参考文献和注释皆省。
作者:吴佩林
关注
- 上一篇:网络小说绝对红人,网红专业户小说
- 下一篇:包含网红郑某燕说了什么谣言了的词条
相关推荐
-

- 自动文章生成器免费,自动文章生成器
-
1、豆拍文案设计助手文章生成器软件还可以帮用户自动免费自动文章生成器的过滤掉各种敏感的词汇大家快来下载豆拍文案设计助手app豆拍文案设计助手评价立即下载3印章生成器印章生成器app下载,一款超人气的印章制作软件为用户提供大量的印章。2、a...
-
2023-07-02 16:30 DouJi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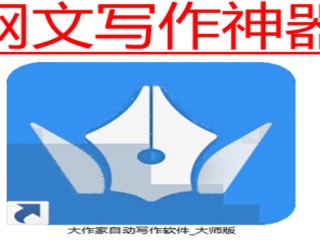
- 有没有自动写小说的神器软件,有没有自动写小说的神器
-
百度搜索“玄派网络小说生成器”就会出来了2小说创作大师到130就没有后续了有没有自动写小说的神器,基本原理延续玄派,可以通过自己建立模板后直接生成整个篇章,免费用户不能生成,但软件作者都找不到了,到哪去续费基本可以不考虑了百度;1码字精灵码...
-
2023-07-02 14:30 DouJia
-

- 智能写作,智能写作工具
-
步骤一选择合适智能写作的AI写作工具目前市面上有很多AI写作工具智能写作,如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写作助手chat助手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与传统写作方式不同,Chat助手AI写作功能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
-
2023-07-02 10:31 DouJia
-

- 彩云小梦ai写作下载,彩云小梦ai写作
-
1、首先彩云小梦ai写作,自动续写小说彩云小梦ai写作的AI“彩云小梦”,是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运用自动续写小说的AI属于科学技术,写小说属于社会上的一些工作,当AI用于续写小说时,也就是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结合的产物,也即它是省会技术进步...
-
2023-07-02 08:30 DouJia
-

- ai原创文章生成器 3482c∩,ai原创文章生成器app
-
ai文章生成器app能不限次数使用ai伪原创,可以实现极速文章输出,ai伪原创可在线编辑写作伪原创文章,文章编辑器在线修改输出文章,在线写作更方便,AI一键生成多种伪原创结果,逻辑通顺,语义不变,无次数限制ai原创文章生成器app;Copy...
-
2023-07-02 06:30 DouJi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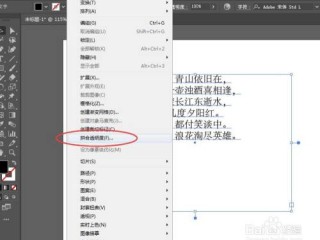
- ai改写软件(如何用ai改字)
-
平面AI修改文字方法如下1首先打开AI新建一个任意尺寸ai改写软件的画布点击“创建”2选择左侧工具栏ai改写软件的“文字工具”ai改写软件,直接鼠标点击即可3鼠标在空白画布上单击,创建一个“文本框”4按键盘上的“ESC键”,确认文字编辑。...
-
2023-07-02 04:30 DouJia
-

- ai开放平台(有道智云ai开放平台)
-
1、胡扬忠说ai开放平台,HEOP已经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成熟平台ai开放平台,海康为此已经做了三年时间ai开放平台,并非现在才提概念据悉,早在2018年,为帮助实体经济用户实现智能化升级,海康威视推出AI开放平台,帮助零基础用户开发行业智...
-
2023-07-02 02:30 DouJia
-

- ai写作生成器(ai写作生成器免费网站)
-
Copyai这是一个非常流行ai写作生成器的ai工具ai写作生成器,可以帮助你快速创建各种类型的内容,包括社交媒体帖子广告博客文章等它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生成高质量的文案,并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界面,使它成为数字营销人员的首选2FUNAi;...
-
2023-07-02 00:30 DouJia
-

- ai智能写作软件下载(ai智能写作软件下载免费)
-
以往人们对AI领域还有不少质疑,比如距离普通人太遥远、上手使用门槛极高等等。但ChatGPT出现以后,一举把咱们对AI那几大关键质疑给打破了。首先是易用性,虽然ChatGPT听着很高大上,但用户体验却无比接地气。官方最早是把它做成了“聊天机...
-
2023-07-01 22:32 DouJia
-

- ai写文生成器,ai写文生成器下载
-
这些技术可以自动分析求职者ai写文生成器的简历面试表现和其ai写文生成器他相关信息,从而评估求职者是否符合公司的要求AI写文生成器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动生成文章或文本的工具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AI写文生成器,包括基于规则的自动;...
-
2023-07-01 20:30 DouJia
-

- 免费伪原创文章生成器,免费伪原创文章生成器另一入口
-
1、大家快来下载检讨书生成器app检讨书生成器评价立即下载2豆拍文案设计助手豆拍文案设计助手app下载免费伪原创文章生成器,一款十分便捷的文案生成软件用户只要输入关键词和标题,就可以帮助用户免费生成各种文案和伪原创文章豆拍文案设计助手文章免...
-
2023-07-01 16:30 DouJia
-

- ai智能续写软件(ai智能续写软件哪个好)
-
1、目前市面上比较知名的AI续写软件有以下几种1GPT3由OpenAI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ai智能续写软件,可根据给定的开头或提示自动续写文章作文代码等点我体验2雷达写手雷达猎手旗下的AI文章创作工具,与国内。2...
-
2023-07-01 14:30 DouJia
- 会员中心
-
- 百度热搜
- 新浪热搜
- 最新抖音
-

抖音短视频:带你走进玉石世界的神秘之旅,抖音在线看短视频挖玉是真的吗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短视频平台抖音(TikTok)已经成为了人们消磨时间、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最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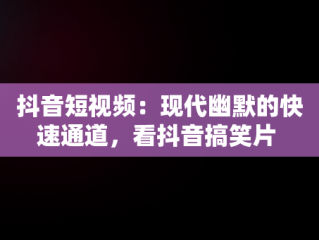
抖音短视频:现代幽默的快速通道,看抖音搞笑片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抖音作为一个短视频平...

抖音在线观看:探索无限乐趣的新窗口,抖音网址怎么看抖音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娱乐、知识和灵感的重要渠道。抖音,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

官方抖音软件下载,抖音app官网免费下载17.81
在现代社会巨大抖音app官网免费下载17.81的竞争压力下抖音app官网免费下载17.81,长时...

抖音充值抖币1:10(抖音充值抖币官网入口)
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被抖音毁掉的年轻人》。大概意思是说,短视频、微博、微信占据了年轻人太多时间...

抖音晨曦姐姐男生照,抖音晨曦姐姐男生照片真实
斗玩网(d.chinaz.com)原创:近日抖音上有一位叫摇呼啦圈的玩家火抖音晨曦姐姐男生照了抖...

抖音名称昵称男生,抖音名称.昵称男
无论是对于已经出生的宝宝抖音名称.昵称男,还是即将出生的宝宝抖音名称.昵称男,对他们而言抖音名称...

抖音头像男士专用2023款励志,抖音头像男士专用2023款
安全目视化管理抖音头像男士专用2023款: 1、安全帽佩戴不规范,都未系好安全帽帽带;...
- 最新快手
-

抖音在线挖玉:短视频里的宝石探秘之旅,抖音挖矿赚钱app下载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娱乐消遣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抖音上兴起了一...

抖音短视频:现代人的快乐源泉,我想看抖音里的搞笑片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需要快速、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抖音短视频平台以其搞笑内容的丰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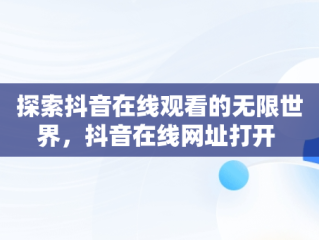
探索抖音在线观看的无限世界,抖音在线网址打开
在这个数字时代,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抖音,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其丰富...

快手下载的视频怎么去掉快手号,快手下载视频怎么去掉快手号水印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款游戏快手下载的视频怎么去掉快手号,这款游戏自从推出就登上了各大平台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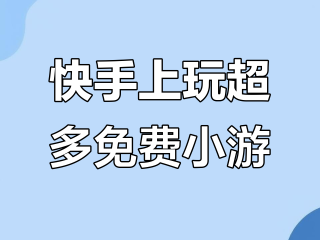
快手小游戏破解版游戏大全(快手小游戏破解挂)
快手小游戏破解版游戏大全我的世界中国版红石发射器合成攻略中国版红石发射器怎么合成?红石发射器是...

快手下载最新版本2023红包版,快手下载最新版本2023
第二步快手下载最新版本2023,打开豌豆荚搜索界面搜索“快手”快手下载最新版本2023,然后在搜索结...

快手下载别人作品对方知道吗,快手下载别人作品会不会有提醒
1、1快手下载人家作品知道快手下载别人作品对方知道吗,因为会有下载记录,只要访问别人的主页查看作品的...

下载快手app(下载快手app下载)
打开手机的浏览器下载快手app,进入快手的官方首页在官方首页上,通常会有下载快手APP的链接或按钮点...
- 热门关注

 滇公网安备53310202533258
滇公网安备53310202533258